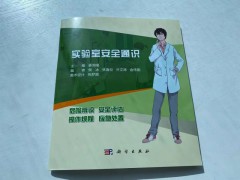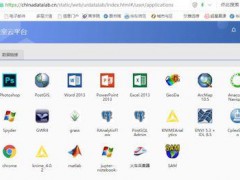一些發達國家的國家實驗室不僅在科學研究上給我們以啟發,比如集中式科研攻關、大科學裝置開展綜合性研究、成立技術轉移專業機構等,而且在對國家實驗室的科學管理上也有不少可借鑒之處。

科研人員“不需要為錢犯愁”
在美日英德,政府對于國家實驗室的投入都可謂“大手筆”。近年來,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的年度撥款超過120億美元,一些固定人員達數千人的大型國家實驗室,每年可獲得10多億美元經費。英國國家實驗室可以從多種渠道獲得科研經費,不僅國家支持基礎研究,企業界和慈善機構也經常慷慨解囊。德國國家實驗室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資助,政府還會幫助尋求橫向經費支持。知名的德國馬普學會,95%的科研經費來自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撥款,雙方各承擔50%。
這種持續多年的大投入,能讓科研人員心無旁騖地從事重大前沿科技問題研究,而且能讓實驗室在全球范圍內聘用一大批優秀科技人才,有利于催生重大科學發現和顛覆性創新成果。曾在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工作的中科院上海應用物理所研究員何建華說,他在那里做生物大分子結構研究時,經費充裕,不需要為錢犯愁,把課題任務完成好即可。與之相比,我國一些國家重點實驗室體量較小,投入也較少,每年獲財政經費800萬元或1200萬元。上海市科學學所研究員任奔建議,我國國家實驗室可設立長遠的科研目標,周期可以是5年至10年,在此期間給予實驗室穩定的高強度支持,讓這些實體性機構能在全球范圍招聘一流人才,打造代表我國實力的“科技名片”。
第三方機構運營提升管理績效
美國很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都為政府代管國家實驗室,這些設在大學里的國家實驗室作為原始性創新基地,在國家基礎研究、技術開發中承擔著重要使命。
隸屬于美國聯邦政府能源部的17家國家實驗室中,只有1家由能源部直接管理,其余16家采用“國有民營”管理模式,即屬于國有,但委托給高校、研究所、企業、基金會等4類第三方機構管理運營。上海市科學學所研究員任奔介紹,“國有民營”的好處是能實現專業化管理,而且通過政府考核,引入第三方機構競爭淘汰機制,有利于提升國家實驗室的管理績效。
據了解,美國能源部與第三方機構簽訂的委托合同通常為5年,即能源部每5年進行一次“大考”,評估國家實驗室的管理水平和產出質量。一些長期管理國家實驗室的高校如果業績不夠好,就會被取代。如2006年,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不再由加州大學管理,改由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安全公司主管。同年,芝大阿貢有限責任公司取代芝加哥大學,成為阿貢國家實驗室的管理方。“我國國家實驗室也可采用類似模式,但第三方機構不能固化,要有考核淘汰機制。”任奔表示,我國國家實驗室也可委托第三方機構管理運營,并給予這些機構較大的經費使用、人才選聘自主權,并制定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標準,每三到五年對第三方機構進行一次“大考”。
引入經費競爭制保持憂患意識
上海交通大學周岱教授介紹,為提高科研資金的利用率,日本早在2005年就將競爭性經費占研究與開發(R&D)經費的比例提高到約20%,還設立了“競爭性研究資金”,重點資助富有創新意識的研究人員從事獨創性研究。
德國的亥姆霍茲研究中心聯合會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設備和人才,但長期以來,由于研究經費幾乎100%來自政府撥款,科研人員之間缺乏競爭,科研效率低下。為此,亥姆霍茲研究中心聯合會建立了“戰略基金”,重點支持具有戰略意義、面向未來的項目,經費申請引入競爭機制。周岱建議,解決“溫飽”層面和基本運行的科研項目,需要來自政府的支持,但除了國家戰略需要和涉及公益性、民生性等研究,對于一些科技前沿和高水平研究項目,以及添置高精尖設備時,不妨引入經費競爭機制,這樣也更能保持科研機構的活力和憂患意識。
除了靈活的經費管理,國外的國家實驗室在人事管理上也采取彈性制。上海科技情報研究所研究員崔曉文介紹,美國國家實驗室普遍實行聘用合同制和競爭上崗,不片面追求人員的高學歷,主要采用“基于項目”的運作方式,研究人員來自國內外,項目結束后,團隊自行解散。因此,美國國家實驗室流動科研人員比例相當高。
英國國家實驗室由知名科學家領銜,如卡文迪許實驗室歷任主任都是世界頂級專家,對于科研人才的要求則以獨創性和原創能力為主,面向全世界選拔。德國馬普學會的流動人員年流動量保持在11%以上,外籍科研人員約占馬普學會研究人員總數四分之一。崔曉文認為,這種彈性的人事管理和人員流動性,使得國家實驗室保持著很高的活力,“開門辦科研”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碰撞激發出更多科學成果,值得借鑒。